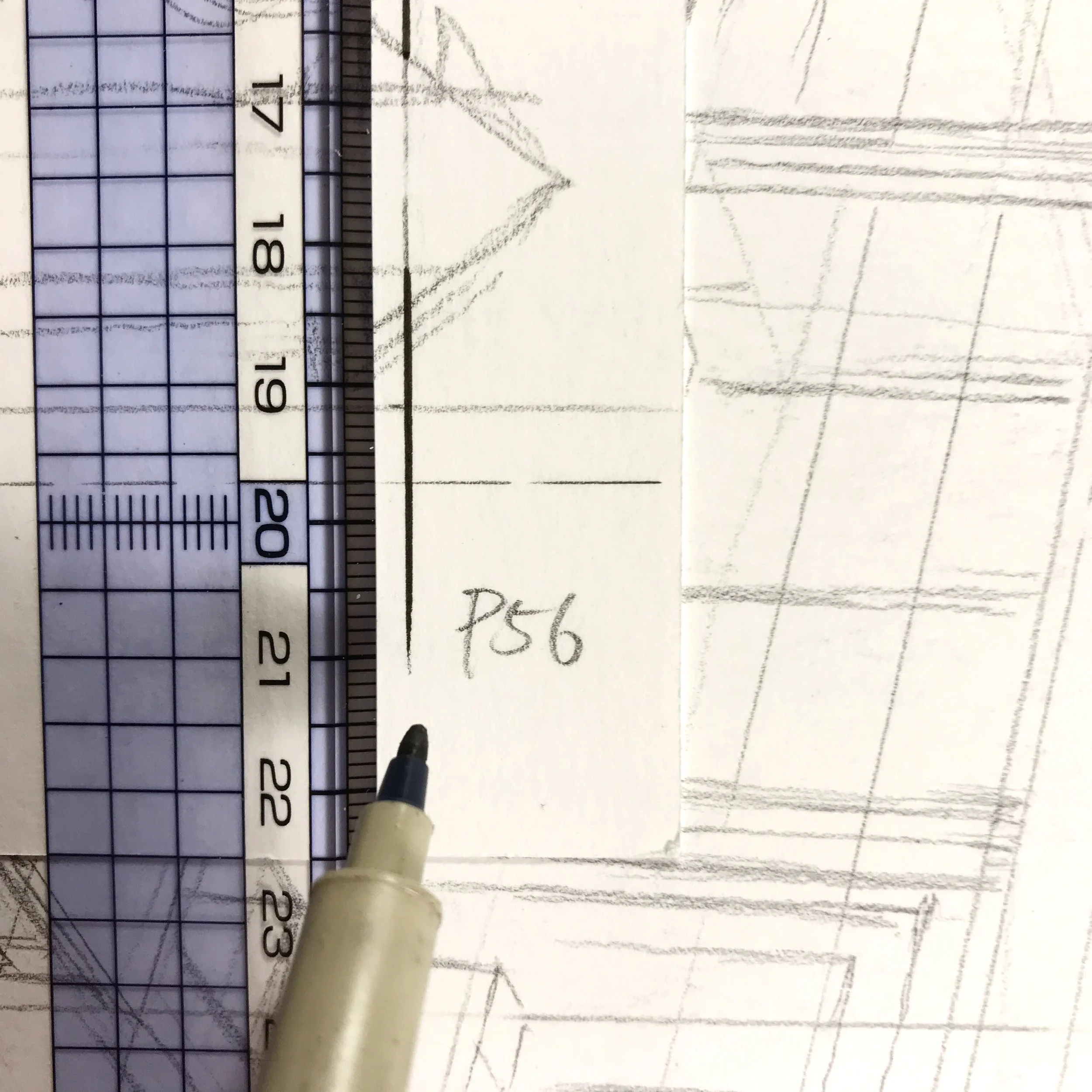前两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突然和一群播客上的听友们群聊了一回。
哇,好久没有像这样和众人交流了!那仿佛是聊天室、MSN、以及短消息的混合谈话,都是不认识的不曾见过面的听友,垂直的聊天界面,人们不停地插各自的话题进来,有的人疯狂歪楼,有的话题乱打岔,还有不时使劲塞相关链接的,一度相当混乱。长久独居数月隔离埋头画画的我,借着这个暂时摆脱了对仍然肆虐的疫情和美国社会的焦虑,兴奋地和大家交换着想法,一时间大脑皮层相当兴奋,玩到深夜,之后躺下,半宿都没睡踏实。
平时里都只是埋头画画,除了跟猫嘟囔几句,往往一整天说不到一句完整的话。漫画家的清静孤寂便是这样,口舌越少,便越能专注在故事的表达上。也因为曾对饭桌上的社交型口水谈话感到无聊透顶,觉得不如干脆回到无声的世界,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连带人声的音乐都不听,沉浸在对故事世界的搭建中。
可是自辛普猴的漫画进入了上色阶段,以及大量的场景绘制部分,脑中一部分语言功能和交流的愿望便又悄悄苏醒了过来,先是要听人唱的歌儿,再是想听人说话,现在到了时不时自言自语,明白过来时屁蛋(我的猫)一脸困惑地看着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成段成段地念叨了半天了。
我并非不喜欢与人说话,同某人在雪夜静聊到天亮的时候也是有的。世间最好的聊天,我觉得是与两三好友,几杯啤酒或茶,每人都有话说,长夜漫谈,畅所欲言。年轻时若没有那样的时光,仿佛根本没有长大呢。
说起雪夜,儿时幸运地读过的《柳林风声》里,其中有一格:鼹鼠和老鼠,在雪地中找到了自己荒废已久的家,窘迫的鼹鼠正愁着自己没有东西招待自己的朋友,老鼠却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串香肠,沙丁鱼罐头和几瓶啤酒,“我们可以办个派对呢!”老鼠开心地说道,鼹鼠也开心起来。后来有人敲门,来了许多唱赞歌的小田鼠们,大家一起围在桌前,围绕在暖融融的桌前渡过了圣诞夜。这个寒夜里的小老鼠洞的画面和文字,成为了我童年极其喜欢的场面之一,对此念念不忘。
这一版的《柳林风声》,由中国连环画作者曾佑玮和张广庆共同绘制,收录在《世界童话名著合集》的第四册当中。
很多年以后,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法语版的《柳林风声》系列,虽然是完全不同的画法,但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癞蛤蟆和他的朋友,那时起知道了法国画家Michel Plessix这个名字。
仔细翻找鼹鼠和老鼠在家找香肠的画面,想看看他是怎么画这页的,但法语漫画的篇幅完全不同,薄薄的一本还没画到那夜故事就结束了。之后又过了好些年,终于在网上找到了后几册。漂洋过海买到手之后,欣喜地翻开,这是他对“雪夜里的鼠聚”此页的描绘:
The Wind in the Willows-Vol.2 Mr.Joad-Michel Plessix
不同的作者,对同样的文本有不同的描绘。在我看来,童年时中国画家那一格虽是黑白的版本,论印刷和细节完全无法与Plessix先生的无法比,但孩童时的我看的那个简陋的版本,却因为童真的想象,仍成为了心中不可替代的美妙的佳作。或许是儿时的贫乏的物质生活,德国香肠,沙丁鱼罐头,饼干和啤酒,变成了我心目中夜宵的最佳搭配,在一张画面里画上各种形状满满当当的物件也变成了特别好玩的爱好。
在这里附上一个豆瓣上对比《柳林风声》各个版本的绘本插图的汇总,请戳这里。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的课堂上讲19世纪英国文学的时候有说过这么一段:狄更斯的小说结尾,失散或久别的亲友又在一起了,总是夜晚,总是壁炉柴火熊熊燃,总是蜡烛、热茶,大家围着那张不大不小的圆桌,你看我,我看你,往事如烟,人生似梦,这种英国式的小团圆,比中国式的大团圆有诗意得多。
哈哈,每次看到这里都大赞木心老师嘴毒!和打着领结、戴着画格子鸭舌帽的19世纪英国绅士的团聚比起来,咱那些“强撑”的家庭聚会确实是矬爆了。可是,吐槽归吐槽,早在中国的东晋,咱《兰亭序》里那种曲溪流水传酒对诗的玩法,不吊打以猎野鸭子为乐的“詹特曼”们一千五百年吗?
想到开去,比起相聚,中国人更珍视离别的情感,毕竟人生聚少离多。荆轲,在灰茫茫的江边,唱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王维,在苍凉的大漠前,念起“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白,在烟花似雨的扬州,甩出“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些动人诗句,却是中国文化里独极具特色的离别之情的精彩表达,套用木心先生的话:独步世界。
如果中国人把道别时彼此相互珍重的诗句,串成珠子,怕是要排到月亮上去,任何一个别的文明都没有这样大规模感叹离别的。我们平日里相处时态度寡淡,不善表达,无论是朋友、爱人、夫妻、父母或是兄弟姐妹,越熟的彼此越难好言相对,有时甚至辅助粗鄙的语言,仿佛那才是符合时宜的话语。可是,所有的情愫、柔软,统统都会在离别时,都会瞬间迸发出来。中国人,总是在集会最热闹美好的时候,就不禁想起离散时的冷清寂寞而哀伤起来。每每这个时候,都恨自己为什么平时不多说些甜话好话,多像西洋人那样闭着眼So proud of you一下,不也挺好吗?也许在离别时,便不至如此伤感,反而如狄更斯们,说走就走那般潇洒,那样下次见面时,才能互相热烈拥抱,相互打量着说:瞧瞧你!
又或者,我们中华民族,是吃尽了甜酸苦辣、经够了分离死别,所以情到深处,汇聚在回眸一瞥中;千言万语,蕴含在一声珍重里。说到底,我们毕竟还是不如那些戴鸭舌帽的海盗的后代的薄情呢。